香菇(散文)
發(fā)布時間:2013-12-20
來源:中國食用菌商務網
捧讀散文大師汪曾祺的文章《昆明食菌》��,滿紙菌香��,不由得想起家鄉(xiāng)磐安的香菇來����。
香菇又名“香蕈”���,是一種高蛋白�、低脂肪的食用菌�����,被譽為“山珍之王”����,是宇航員必備的“太空食品”。磐安山高谷深��,風景清麗����,遍地生菌。隨意出沒的香菇�,就像一篇散落在深山老林中的散文,雋永��、雅美���。生于斯�、長于斯的磐安人����,種菇�����,賣菇�����,吃的是香菇菜�,住的是“香菇樓”���,還留下了香菇的由來和羊 因食菇成仙的美麗傳說�����。
大盤山是浙中名山�����,奇峰聳立����,巨石突兀����,巖洞幽深����,飛瀑懸掛�,溪流潺潺。很早以前����,大盤山腳住著父女倆,女兒叫香菇�,生就一副花容月貌。為避財主逼婚��,她逃進深山密林��。財主的家丁發(fā)現后��,追捕至懸崖絕壁���。這時���,一位仙翁變成美麗的錦雞架著她飛到一棵樹上���。家丁用亂箭射之,香菇與錦雞悠然不見����,那棵樹卻被射得傷痕累累而枯死。翌年春天�����,樹上的一個個傷疤長出了一朵朵褐色的����、像小傘似的菇來,香味撲鼻����,人們都說它是香菇的化身,故取名為“香菇”����。
食菇成仙的羊(公元805——��?)����,山東泰山人�����,唐武宗時代曾任嘉州夾江尉���。后因楊弁之亂,他辭官來到大盤山隱居�����,經常采摘一種狀若“簦”的野菇為食��。日積月累���,羊須發(fā)如漆����,面若童顏�����,步輕如飛。那時�����,羊的哥哥羊忱在臺州樂安當縣令�,每當“往樂安看之,一日而返����。又往天臺,亦一日而返����。日行三四百里”。羊還常去雁蕩等地云游��,均能輕捷如“乘云”��。因來無影去無蹤���,羊就成了傳說中的神仙����。
羊采食的“簦”物�,其實就是野生香菇。明清兩代的《縉云縣志》和1921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《中國人名大辭典》都有這方面的簡略記述��。據傳�,自從羊食菇成仙后,磐安先民認識了這種“長壽菜”��,便開始了人工栽培香菇�。
香菇的傳說美麗動人,香菇的菜肴鮮美誘人����。普通家庭通常把香菇用做配料��,吊吊主料的鮮味���,就像明末清初的美食家袁枚所說:“蕈置各菜中����,皆能助鮮����。”李漁在著名的《閑情偶寄》中��,認為蕈是除筍之外的至鮮至美之物�。“此物素食固佳���,伴以少許葷食尤佳��,蓋蕈之清香有限���,而汁之鮮味無窮"�����。也許受李漁的啟發(fā)�����,用香菇烹制的清湯是久負盛名的宴席“壓腳菜”��,清口解渴�,消化積食,有“無筍難配料�����,無菇不成席”之說�。我國一著名營養(yǎng)學家也曾說過:吃“四條腿”(豬、牛��、羊等)的�����,不如吃“兩條腿”(雞����、鴨�����、鵝等)的�����;吃“兩條腿”的,不如吃“一條腿”(指菇類��,如香菇��、蘑菇等)和“沒有腿”的(指魚類)����。營養(yǎng)學家提倡吃菇類,旨在改善人們的食物結構�,減少“三高”(高血脂、高血糖����、高血壓)疾病的發(fā)生。
磐安香菇菌帽厚實�����,菌褶細密��,菌柄粗短柔軟��,是“菇中極品”�����。到菜市場里轉轉,那香菇��,小的玲瓏可愛�����,大的肥碩飽滿�����,用它為主料做出來的菜肴香鮮絕倫���,令人“愛不釋口”���。在我的印象中,磐安的大小賓館飯店��,有兩道香菇菜做得頗為地道�。一道是“油燜香菇”。將鮮香菇剪蒂洗凈�,用漏勺將瀝干備用的鮮香菇放入滾燙的油鍋中炸出香味(約八成熟)�����,留鍋底油,下精鹽���、味精��、醬油和勾芡的淀粉水�,倒入炸好的香菇�,翻炒至熟,淋上麻油��,迅速起鍋裝盤即成�����。夾一片嘗嘗����,這油燜香菇外表脆嫩,里層香鮮�����,老少皆宜����。前不久����,一批杭州客人來磐采風����,連吃兩盤還不過癮,一副大快朵頤的模樣����。另一道是“炒三絲”,主料分別是牛肉絲�����、青椒絲和適當多的香菇柄絲�。先生炒牛肉絲,再倒入菇柄絲�、料酒、醬油���、紅糖���。燜一會兒,開鍋放入青椒絲,略翻幾下���,即可盛碟。粗粗一看��,牛肉絲和菇柄絲本來都是紅褐色的�����,相差不大�,又經那稠而又稠的醬油、紅糖汁一勾芡���,混若一物��,豈不是大雜燴�?且慢���,還有那蔥翠欲滴的青椒絲呢��,只一“色”字就吊人胃口了����。嚼在嘴里清爽可口����,齒頰留香����,頗有余味�,可謂“至味”。
磐安的山水是綠色的����,人文的,也是生態(tài)的����。到磐安來休閑度假,山水可以不看����,但香菇不能不吃,因為它已在大山深處生長了千百年��,朵朵凝結著山川草木之精華����。當游客離開磐安的時候,也許對磐安山水沒有太多的印象,但帶走的必定是香菇的記憶��。( 作者: 潘江濤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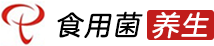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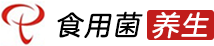
 熱門菜譜
熱門菜譜